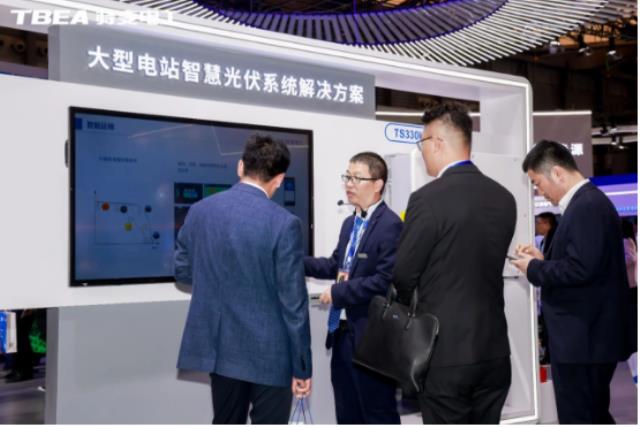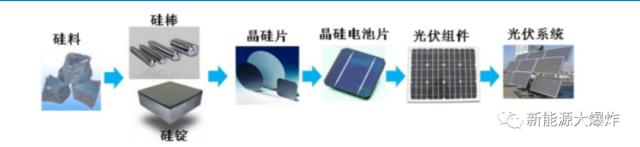近日,不止一家光伏企業被媒體圍攻。
有財務經營壓力,有商業糾紛。企業焦頭爛額,疲于公關,偶爾有個“愣頭青”,反唇相譏,于是雙方打得有來有往,引得群眾吃瓜圍觀。

在這兒我想說:我們媒體人,不要變成賞金獵人。
2010年,我面試了一位曾經在北京一家媒體工作的記者,他問我:“你們是做好還是做壞的?”這讓我很茫然。
有一次我去一家不怎么接觸媒體的企業拜訪,企業人員告訴我:“我們很怕媒體,怕他們不知道哪里不滿意就挖我們的負面。”這讓我覺得很羞恥。我確實見過很多同仁有種莫名的優越感,也確實有認為企業怠慢就有不滿的聲音發出,甚至也有相約爆該企業黑料的。
但我們能不能想一下,企業為什么要尊敬我們?它尊不尊敬我們和我們的職業操守有什么半毛錢關系?
這個世界不應該是這樣的,做媒體也不應該是這樣的。如果負笈求學寒窗多年,工作十余載,在最黃金的年齡,讀書人的風骨卻丟了,這叫怎么一回事?
我們還有機會,把這種恐懼轉為尊敬,當然,也有能力把這種恐懼轉化成唾棄。選擇權,其實一直在我們手里。
或許你會說這些企業真實存在問題,在這里我并不否認。但媒體在報道中用幾個字眼調整就能看出媒體是善意、中立還是惡意,做企業,做光伏企業已經很難了,絕大多數光伏企業家都具備企業家精神,國家剛提出保護企業家,現在就這么HWB一樣圍攻企業,合適么?
我非常尊敬有新聞理想的記者,尤其是調查記者,常常身不能至,心向往之,恨不能和他們一起戰斗在一線。目前中國的調查記者不足百人,群體岌岌可危。其中可能還有專門爆黑料擭取利益而混進調查記者隊伍的敗類。

資深傳媒人李海鵬曾經寫過篇長微博,談為什么再也沒有深度記者,也沒有新聞理想了。“支持一個人去做調查記者的,不是錢,是被尊重感、榮譽感,是真相至上的信念,還有一個,就是這個人可以感覺自己很酷。一個調查記者,前往貧瘠苦難之地,做困難的工作,他是新聞業這座燈塔上的一束微光,同時他也是一個探險者,一個有魅力的人,正是這種自我幻想,以及了雖然不多但總算還有的來自陌生人甚至異性的同樣的幻想,支撐了全球的調查記者們。”
說的真好。
在國外媒體的報道中,我常常看到傲慢、偏見還有對中國的膚淺理解,而在中國,我卻看到貪婪。一位前調查記者說:“最后,記者監督什么最安全呢?——監督大公司,打一下阿里巴巴,它就來投廣告,打一下京東,它就來求刪稿,現在只有大公司好欺負嘛……”
孔夫子有句名言:“見賢思齊焉。”其實后面還有半句:“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。”
絕大多數企業不是裘千仞,我們也不是洪七公。我們媒體尤其是光伏行業媒體,應該是促進這個產業健康發展為目的。作惡的媒體人已經逼死了張國榮,邁克杰克遜,還要來戕害光伏企業嗎?
即使最不喜歡的企業,但看到他們真的每年花大量的真金白銀在做研發時,我也心存一份尊敬。
為了幾千塊錢稿費或者額度更高一點的贊助費用,就可能給企業帶來的就是上億甚至更多的損失,于心何忍?媒體的監督職能不應該是在利益的驅使下,那樣比企業作惡更甚。
墮落的律師被稱為訟棍,喪失了理想的記者又叫什么?

我很惆帳。記者曾經被稱為“無冕之王”,但現在,我感覺我們這個群體是年紀漸長的泰森,那個喪失了榮耀的拳王,在酒吧里盲目的揮舞著拳頭,賺取今夜用于買醉的酬勞。